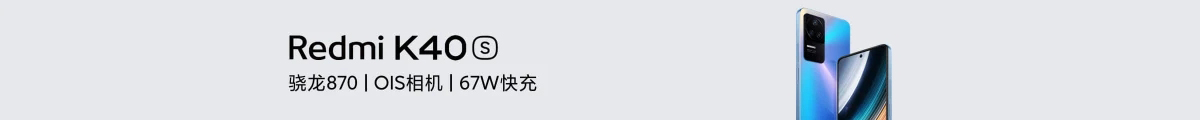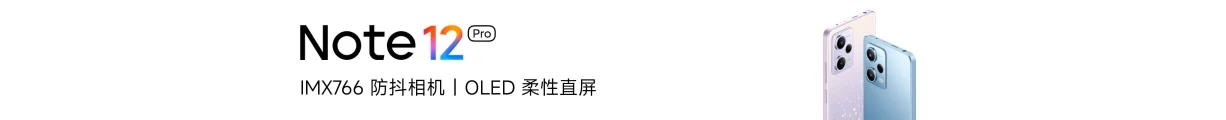体栽:小说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类型:社会批判
时间;19世纪晚期
地点:俄国
初版:1899年主要角色: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卡捷琳娜・米海洛娃・玛丝洛娃(卡秋莎),妓女弗拉基米尔・西蒙松,政治犯
薇拉・波戈仁霍芙斯卡雅,政治犯
短评
《复活》堪称俄国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它非常生动地记录了该时代的人们及其环境,尖锐地揭鲽了官场的卑鄙腐败,把一些小人物的虚荣心表现得惟妙惟肖,还辛辣地讽刺了注重形式的正统观念的虚伪。在托尔斯泰看来,一个人一旦开始昧着良心、自私自利,就会干坏事。这部小说的社会主题是讲社会组织的缺点,个人主题则涉及到宽恕;这是典型的托尔斯泰形式:部分是出于无知而犯下罪孽,这爨露了人性的弱点,紧接着则是通过长期的灵魂的洗涤来赎罪。
概要
卡捷琳娜・玛丝洛娃,,人们一般都叫她卡秋莎,正被从监狱押解到法庭上因谋杀罪受审。她是个私生子,富有的索菲雅・伊凡诺芙娜和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收养了她,这姊妹俩负责照顾和教育她。卡秋莎16岁的时候,她的监护人的侄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了她。当她知
道自己就要做母亲后。便搬到乡下一个接生婆那儿去住。她的孩子一出生,就被送进了育婴堂,不久便死了。卡秋莎受尽各种磨难之后,沦为妓女。在她26岁的时候,被指控跟别人合伙谋害位西伯利亚商人,盗取钱财,正当卡秋莎被押解去法庭的时候,当年诱奸她的聂赫留朵夫正躺在床上想自己的心思。尽管他-一-直跟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却又准备答应跟玛丽雅
・柯察金娜公爵小姐结婚。他也在考虑怎样出卖-些土地给农民。聂赫留朵夫起来后,才想起自己这天要去法院担任刑事庭的陪审员。在法庭上,聂赫留朵夫吃惊地发现被告是卡秋莎,她被诬告合谋盗窃并毒死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商人。审判简直令人作呕,因为那帮官吏自私透顶,愚蠢而又自负,拘泥于形式而不真正关心判决是否公正。聂赫留朵夫念大学时曾在姑姊家佳了一个夏天,在那儿开始认识并喜欢上了卡秋莎。他给她书看,最后爱上了她。三年后他又回到姑姑家时,军队生活使他成了荒淫无度的利己主义者,他诱奸厂卡秋莎。第二天,他给了她一些钱,就回部队去了。等战争结束他又回姑姑家的时候,他得知卡秋莎已怀孕离开那儿了。为了稍稍宽慰自己,他就尽量忘掉她。此时在法庭上看见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心里涌起一种既憎恶又怜悯的复杂情感。起初,他担心外人知道他和她的关系,但卡秋莎没有认出他来,随后他又开始为白己使她陷入这种境地感到懊悔。由于陪审团疏忽大意、无罪的玛丝洛娃被判发送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聂赫留朵夫良心上感到很不安,便决定找律师谈谈被告上诉的可能性。
此后,当聂赫留朵夫和柯察金娜在一起时,他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空虚而又可耻,深感需要净化自己的灵魂,他决定跟卡秋莎结婚,并放弃自己的土地。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卡秋莎,说明自己是谁,但她对他很冷淡。她似乎还对自己妓女的地位感到自豪,因为只有这才能给她空虚的生活带来一丁点儿意义。下一次探监的时候,她在他面前举止很粗俗,当他说要跟她结婚时,她对他很恼怒,转身便回牢房去了。再次去监狱时,聂赫留朵夫被告知说卡秋莎今天不便于会客,因为她用他给的钱买酒喝得大醉。他随后便去看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雅,她是他所认识的一位革命者,曾从狱中给他写过信。他很惊讶,微拉竟非常自豪,决心为革命事业作出牺牲。薇拉劝他疏通下,把卡秋莎调到监狱医院里做护士,让她的处境好一点。聂赫留朵夫便设法替卡秋莎调动,这时聂赫留朵夫已失去了先前期望和卡秋莎结婚的欢乐心情。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执行他的计划,为了给他远行西伯利亚作准备,他先去料理他的地产。在巴诺沃,他目睹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并见到了卡秋莎的姨母玛特廖娜・哈琳娜,打听到他那个在育婴堂死去的孩子的一些情况。他放弃了自己在巴诺沃的土地的所有权,让农民以村庄形式共同拥有那些土地,他由
此体验到一种极大的快乐。
聂赫留朵夫随后便去了圣彼得堡。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卡秋莎的案件向枢密院提出上诉,并设法使无辜的莉迪雅・舒斯托娃获释,她是薇拉・波戈杜覆芙斯卡雅的朋友。来到圣彼得堡后,他就进了他姨母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查尔斯卡雅的贵族圈子,她声称对福彦传道感兴趣,但对世人的不幸命运毫无怜悯之心。聂赫留朵夫为自己上诉的事情在圣彼得堡见了各种各样的大人物。次日他得知莉迪雅・舒斯托娃巴被释放。枢密院决定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但只是因为有个枢密官自称是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在此案中聂赫留朵夫的品行可恶之至.卡秋莎案便维持原判。在这同一天,聂赫留朵夫遇见了他的老朋友谢列宁。此人聪明、诚实,现在是个检察官,但他却不得不向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及其准则屈服。聂赫留朵夫开始看出所有这些官僚都遵循同样的准则:宁可惩办无辜,也不放过一个罪人。一回到奠斯科,聂赫留朵夫便去看卡秋莎,让她在准备递交给皇帝的状子上签字。在探监过程中,他心里再次萌出爱情。卡秋莎也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但她认为跟她这样的人结婚对他不利。在聂赫留朵夫为跟卡秋莎一起动身去西伯利亚作准备时,他开始研究和考虑刑法的性质。然而尽管他阅读了涉及这个题目的大量书籍,但对某些人有什么权利惩罚另一些人的问题却没有找到答案。他也开始认识到合理的惩罚只有体罚和死刑两种,这固然不宜,但至少还有效验,而监禁则完全是不幸。
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漫长路途中,聂赫留朵夫一直跟着犯人并尽可能跟卡秋莎见面。他也看到了被流放者的可怕境遇.聂赫留朵夫对卡秋莎产生了新的爱,一种亲切和怜惜的感情。自从卡秋莎调到政治犯队伍中去后,聂赫留朵夫也逐渐了解到革命者的主要观点,有个名叫弗拉基米尔・西蒙松的政治犯爱上了卡秋莎,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想跟卡秋莎结婚。但她希望征得聂赫留朵夫的同意再决定。聂赫留朵夫说,他为卡秋莎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感到高兴。当卡秋莎知道聂赫留朵夫的答复后,对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东西伯利亚一个偏僻的城市,聂赫留朵夫镯取了自己的信件,得知卡秋莎的苦役刑已改为在西伯利亚较近之处流放,当他去告诉卡秋涉这个消息时,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家庭。卡秋莎说她宁愿跟西蒙松一起生活,她拒绝说她爱他。她告诉聂赫留朵夫,他该去过自己的生活,聂赫留朵夫不觉体验到一种失落感。他感到自己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他明白了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试图纠正坏事的人自己就坏;社会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一套惩罚制度,而是因为人们在相怜相爱。他第一-次看出〈登山训众》(《马太福音》第五章)才真正是实际可行的戒律。从这天晚上起,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赏析:
托尔斯泰的《复活》最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深刻地揭露了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小说在聂赫留朵夫追求正义和灵魂赎罪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了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小说第二个中心点是个人地位对聂赫留朵夫哲学政治观点的转变,特别是对他和卡秋莎的关系的影响,没有卡秋莎,也就无从谈起聂赫留朵夫的重新觉醒和自我牺牲,
在学生时代,聂赫留朵夫以理想主义者的眼光看待世事,相信万事万物可臻完善,否认土地私有制。然而,军队生活混灭了他的理想主义,他很快便放弃了为美好事业献身的思想。他抛弃了卡秋莎,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价值标准,以便建立公众心目中贵族的形象。直到十年以后在审判卡秋莎时,他才良心猛醒,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疑问,认识到自已对卡秋莎犯下的罪孽,决定全力为她奔走鸣冤,从灵魂深处开始赎罪。聂赫留朵夫因而把人看作是二元的一一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他极力排斥那种导致他犯罪的兽性本能。他意识到即使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于是他便在自己内心正义感的驱使下纠正自已犯下的过失。他的这-一
复活过程是耐人寻昧的。
聂赫留朵夫在深入农村、监狱的过程中,始认识到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公正,无辜者被错误地监禁,政治犯只不过是因为持有不同的观点,一帮泥瓦工只因出外打短工护照过期而被监禁,他们曾一起向聂赫留朵夫求助。
聂赫留朵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社会环境导致了犯罪,而不是所谓的犯人对社会犯了罪,他否认那种依据个人或阶段特征判定天生堕落的说法。聂赫留朵夫进而认识到广大农民之所以无权、贫困、饥饿、病弱,甚而犯罪,都是那些权贵造成的,权贵们企图以此维护他们凭借特权占有的财富。政府和科学声称要改善这种状况,但实际上根本不考虑问题的根源。他发现扭转这种状况的唯一方法是把土地还给耕种它们的农民。但当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土地送给农民时,他的家人和上流社会的朋友却优虑他精神是否正常,连那些农民也用敌对狐疑的眼光看待此举。聂赫留朵夫对不公正原因的探究使他心头始终萦绕一个问题,就是真理是否在法律中起作用。在他看来,很明显,法律无论是通过判决或法庭上的审判都未把真理考虑在内,尽管这个概念一般人都普適接受。那么,事实如何呢?聂赫留朵夫得出结论,法律的目的只不过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些执法者以及法律所迎合的人和法律审判的对象同祥有罪。法律体系最基本的荒谬在于相信有些人有权利审判另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强调坏人不能审判坏人,审判和惩罚不但有害、残忍和不道德.而且也没有效验。他认定,现行社会制度根本谈不上公
正。尽管有合法的和非法的犯罪行为,而社会和般秩序终究能存在,只是因为人们仍旧在相怜相爱,
小说的情节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和卡秋莎灵魂上的重新觉醒平行发展的。在她被定罪后和聂赫留朵夫第一次重新会面时,她抑制住自己的痛苦,尽量不去回忆年轻时怎祥被聂赫留朵夫诱奸又被残忍地抛弃。此外,她对自己为生活所迫去当妓女已渐渐变得麻木起来。聂赫留朵夫意识到自己对她犯下的罪恶比他知道的还要大得多,他看出卡秋莎已经死去,只剩下玛丝洛娃了。尽管聂赫留朵夫决定不但要为卡秋莎获得自由奔波,而且要对她灵魂复活负责,但他的影响只是使卡秋莎新生的因素之一。卡秋莎感到聂赫留朵夫正在再次利用她,但因他坚持为她奔走效劳,她对他的旧情又复燃了。随后她为了不损害他的地位又牺牲了自己的爱。这样卡秋莎第三次承接了聂赫留朵夫肩头的担子:第一次被他诱奸为他生了私生子;其后又允许他为她作出牺牲;最后为了使他摆脱跟她结婚的承诺,她又否认了对他的爱。虽然如此,小说的主要着眼点仍是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就聂赫留朵夫的个人关系而言,他对社会的叛逆以及灵魂再生过程是最不令人信服的。他在欺骗卡秋莎又设法营敉她这一转变过程中,先是欺骗她而获得肉体上的满足,随后又利用她进行灵魂上的赎罪。他仍以太上皇的面目出现,他的专断妨碍了相互间交换意见。他自称像耶稣一样,不是以主人而是以仆人的眼光看自己,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专横的仆人。他没有讲一句抚爱的话就主动提出跟卡秋莎结婚,他这种自我牺牲无疑是强加给她沉重的负担。看来聂赫留朵夫主要关心的是从自卑中得到美好的情感一一那怕是以自虐狂的形式。聂赫留朵夫声称他将尽力在自己良心上听从上帝的意志;实现这个许诺,他便可求得安宁。
聂赫留朵夫复活的最后一步,也可说真正的第一步是被基督教《福音》所启示,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人的唯一义务就是执行福音书中的种种戒律,但又无须官方教会的指导,他们只注重仪式。聂赫留朵夫认为教会跟社会上其他机构一样腐败不堪。.比如,牧师在法庭宣誓作证时带着妄自尊大的神气,却并不对审判是否公正提出疑义。带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赶到监狱教堂的犯人却去替压迫他们的政权祈祷,而玩世术恭、信奉异教的祭司以“这对他们有用”的借口把人们导入蒙昧的迷信之中。聂赫留朵夫像鄙视自己过去的生活及其所代表的东西一样,极端厌恶这种虚伪的宗教。他个人对条教的这种态度促使他深刻而富有革命性地认识和理解社会与正义一托尔斯秦本人想必也费成这种理解。
玛丽・皮斯・芬利
(万仕同详王新周庆陈方明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