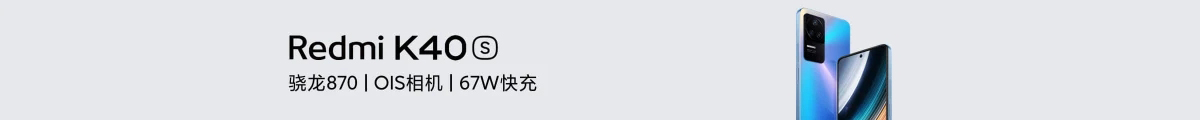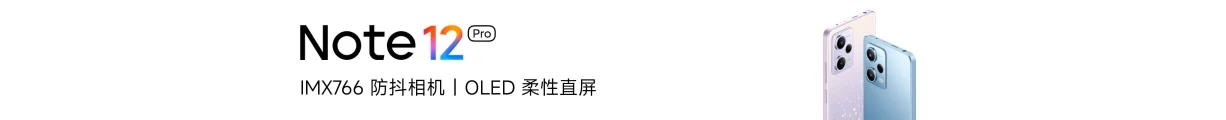体裁:小说
作者: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
类型:社会编年史
时间:约 1815 年至 1835 年地点:法国
初版:1862年
主要角色:
冉阿让,又名马德兰市长
芳汀,受冉阿让帮助的女工
珂赛特,芳汀之女
沙威,警方侦探
马吕斯·彭眉胥,珂赛特的恋人及丈夫
德纳第先生,又名容德雷特,无赖
爱泼妮娜·德纳第,德纳第之女
短评:
《悲惨世界》是一部情节扣人心弦的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一说研究贫困与赤贫生活的社会学作品。维克多·雨果花了 14 年时间才写就了这部巨著,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该小说如此枝叶繁复。这篇小说主要叙述了罪犯冉阿让的生活经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高度激化,这引起了作者的深切关注。冉阿让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社会中的苦难人的典型。《悲惨世界》既是一部庞大的社会史录,又是一部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叙事小说。它是雨果的代表作,也是世界名著之一。
概要:
1815年在法国,一位名叫冉阿让的苦役犯在蹲了19年的牢房后被释放了。当初他为使他姐姐的一家人免受饥饿的折磨偷了一片面包而被判了五年徒刑,后来由于他屡次越狱逃跑刑期被延长。在服刑期间,他过人的膂
力令别的犯人惊讶不已。
刑满释放后,他步行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客栈老板从他那发黄的通行证上看出他曾是一个犯人,因此不卖给他吃的,也不让他留宿。无奈,他来到狄涅城主教家。主教是一位圣人,待他很好,供他吃住。但是,当天晚上,冉阿让偷了主教的银器逃跑了。然而,他很快又被警方抓回主教面前。主教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还把银器赠送给了他,并另赠一对银烛台。目瞪口呆的警察只得放了冉阿让,当冉阿让与主教单独在一起时,主教让冉阿让拿着银器与银烛台去过诚实的生活。冉阿让茫然了。
1817年,巴黎住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名叫芳汀。她有一私生女,名叫珂赛特,寄养在德纳第夫妇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德纳第夫妇向芳汀索要的抚养费越来越高,但对珂赛特的虐待则与日俱增,甚至不供给她必要的生活用品。芳汀无可奈何,来到了蒙特漪镇,在马德兰开的一家玻璃厂当工人。马德兰是一位善良、慷慨的老板。他的来历无人知晓,但他的乐善好施则是尽人皆知的。他来蒙特漪镇时,只是一个穷困的苦力,后来一项偶然的发明使他得以自立门户,他开了一座玻璃厂,雇了许多工人。五年后,他被推选为所在市的市长,市民对其爱戴备至。据传他膂力过人。这时,唯有一个人,就是警方侦探沙威,对他心怀疑忌,密切注视。沙威出生于狱中,这对他的生活影响极大。他对职业的狂热态度令人不寒而栗。他决心调查马德兰的来历。一天,他看到马德兰用背顶起一辆马车,救了压在车底下的一位老汉的性命,他若有所悟,他记得以前有个名叫冉阿让的苦役犯也有如此神力。芳汀从没告诉任何人她有个私生女。但这消息却不胫而走,在厂里传播开来。她因此被解雇了。马德兰对此一无所知。后来,她为支付德纳第一家索要的越来越高的抚养费,被迫沦为娼妓。一天晚上,当她在街上拉客的时候被沙威抓住了,马德兰听说她的悲惨遭遇和她患有肺病后,把她送进医院,并答应让他们母女团聚。马德兰正准备去接珂赛特,沙威来向他坦白,说自己曾向巴黎警方误报马德兰就是以前的苦役犯冉阿让,还说,真正的冉阿让用着假名,已在阿拉斯被捕了,两日后开庭审理他的案子。
当天夜里,马德兰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冉阿让。他不愿让一名无辜者受害,于是赶到阿拉斯参加了审判会,并在会上宣称他是真正的冉阿让。他把住址留给法官后,即去医院探望芳汀。沙威跟踪而来,将他强行逮捕。眼看搭救自己的人被捕,芳汀气绝身亡。
冉阿让入狱的第二天就逃跑了,不久,他又为沙威抓获。但他又一次越狱逃跑了。不久他把八岁的的珂赛特从德纳第家领走了。他渐渐地疼爱起这个女孩来。他们一起在巴黎市郊的戈尔波租了房子住了下来。当沙威寻踪而来时,冉阿让携孩子逃到了一家修道院。在那儿冉阿让曾从马车底下救出性命的农民老汉搭救了他们。老汉现在是修道院园林工,他让冉阿让做他
的帮手,把珂赛特安排在修道院的学校里读书。
数年过去了,冉阿让带着完成学业的珂赛特来到了巴黎,在一条狭小僻静的街上租了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邻人似乎对这一老一少不怎么关心,与此同时,无赖德纳第携家小搬到了戈尔波。他这时化名叫容德雷特。他的隔壁住着一位名叫马吕斯·彭眉胥的青年律师,马吕斯思想进步,因此与其保守的外祖父闹翻了。他的父亲原是一位军官,在滑铁卢战役中他以为德纳第救过他,临死时嘱咐儿子日后要好好报答德纳第,马吕斯没有想到这位容德雷特就是当年父亲的救命恩人。当容德雷特一家因付不起房租要被赶走时,马吕斯用自己微薄的积蓄给他们付了房租。
一天晚上,马吕斯在外散步时遇到了珂赛特与冉阿让。从那以后他渐渐地爱上了这位经常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为伴的姑娘。最后他跟踪来到她的住处。冉阿让对马吕斯警惕起来。为防不测,他带着珂赛特搬家了。一天上午,马吕斯收到爱泼妮娜·容德雷特的一封信。从信中,他了解到,这家人又在求他救济。他对这家人起了疑心。透过墙上的一个洞孔,马吕斯听到容德雷特说其恩人要来。人来以后,马吕斯认出容德雷特所谓的恩人就是与珂赛特在一起的老头。他从爱泼妮娜的口中获悉了珂赛特的住址。他还偷听到容德雷特一家正密谋勒索那位以为是珂赛特父亲的老头。马吕斯非常害怕,并把他们的密谋告诉了侦探沙威。
当冉阿让来给容德雷特送钱时,马吕斯通过墙上的洞孔窥视着,正当他们谈话时,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出现了。容德雷特坦白地承认他的真名叫德纳第。马吕斯恐慌起来,不知该保护父亲的恩人,还是保护珂赛特的父亲。在德纳第的威胁下,冉阿让答应派人找他的女儿再要些钱,但是他把假地址给了德纳第。当骗局揭穿以后,强盗们威胁要杀了冉阿让。马吕斯从洞孔中扔进了一张纸条,提请冉阿让注意,就在这时沙威出现了,他只逮到了其他人,却没有抓到冉阿让,他越窗逃跑了。
马吕斯找到了珂赛特的住处。一天晚上,珂赛特告诉他,她和父亲即将去英国。马吕斯请求他的外祖父同意他与珂赛特的婚事,可是被拒绝了。他绝望而归,发现珂赛特的住处已人去楼空了。他在那儿遇到爱泼妮娜,她告诉他,他那些革命的朋友已经开始起义了,他们正在街垒边等着他。珂赛特既走,马吕斯欣然随爱泼妮娜来到街垒边。到了那儿,他看到沙威被作为奸细捆绑着。在战斗中,爱泼妮娜舍身救了马吕斯。临死时,她把珂赛特让她转交的信交给了马吕斯。在信中珂赛特留下了自己的住址。马吕斯给珂赛特回信说,他的外祖父不同意他的婚事,他本人又没钱结婚,而且还可能在街垒战斗中牺牲。冉阿让读到了这封信,奔街垒而来。他看到沙威被革命军捆绑着,于是给他松了绑。街垒失守了。冉阿让怀着混乱的心情来到了受伤的马吕斯跟前,背起他躲进了巴黎的下水道。
经过数小时的徘徊,冉阿让背着马吕斯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出口处的门锁着。德纳第站在门口。由于光线不足,冉阿让没认出他来。德纳第要内阿让交些钱作为开门的代价。出来以后,冉阿让遇到了沙威。沙威还想拘捕他。冉阿让恳求沙威让他先把马吕斯送到他的外祖父家。沙威同意了,并在门边等候。突然,他转身向河边冲去。他既不愿渎职,又不忍再把救过自己性命的恩人投进监牢,于是投入塞纳河自尽了。
马吕斯康复后即同珂赛特结了婚。冉阿让给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珂赛特这时才了解到冉阿让并不是她的生父。冉阿让告诉马吕斯,他是一个人们早已以为死了的逃犯,并恳求马吕斯同意他偶尔来看望珂赛特。但是,渐渐地,马吕斯不让冉阿让进屋了,当马吕斯从德纳第口中得知是冉阿让从街垒边救出自己时,他携珂赛特一起,急忙赶到冉阿让的住处。此时的冉阿让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看到他们,他相信这对年轻人是爱他的,也相信自己的过去是清白的。临终时,他把主教送给自己的一对烛台交给了珂赛特,用尽最后一口气说,他的一生都是努力按照狄涅城主教的希望过的。他死后被埋葬了,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赏析:
就情节而言,《悲惨世界》基本上是一部侦探小说,但同时,它又巧妙地将戏剧性情节与道德训诫融合为一体。作品充满难以置信的巧合,超乎寻常的人类情感,以及巨人般的英雄形象。然而他仍不失其真情实感,读来感人至深。《悲惨世界》是一部歌颂巴黎人民事迹的长篇史诗,同时它又出神入化地再现了千姿百态的巴黎下层社会生活,使人联想起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人物繁杂,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小说作品。本书扣人心弦的情节所揭示的很显然是人们与邪恶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主题,但就总体而论,它却更着力于戏剧性地表现人生之变幻沧桑。
雨果宣称,这是一部“富有宗教色彩”的小说,而宗教意识的确在作品中起着重要作用。小说开篇就展示了善与恶的斗争。在作品中起着同样重要作用的是命运,或说是“宿命”的主题。在作者笔下,无论我们人类如何处心积虑地破译命运之谜,“宿命之黑色脉络”总会不断地显现出来,只要人们一息尚存,他们永远不会清楚地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摆脱不了命运的戏弄,也摆脱不了与命运看来是永无休止的抗争。
《悲惨世界》之所以备受读者喜爱,也许与其情节发展急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戏剧性,甚至是无法料想的变化,其中许多章节继承了19世纪戏剧的传统,叙述到紧张之处嘎然而止,具有这种传统的戏剧,雨果本人也曾写过,尽管故事情节枝杈横生却发展迅速,读来令人感到仿佛在观看一群不同的角色在田间、在巴黎街巷中赛跑,另人激奋不已。
小说虽说在规模上堪称巨著,甚至堪称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史诗,在人物驱使,对此作者清楚地解释道,他们的心灵受到早年生活经历和社会的扭曲,尽管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但书中有很多地方与数十年后才出现的自然主义流派不谋而合。
的刻画上却又真实可信,其中很多人物看上去像是着了魔,或是受着仇恨的或许书中最令人感到恐怖和紧张的人物就是警探沙威,他似乎无处不在。沙威是个精明的人,但他并不具有智慧。他的一生毁于那些心胸狭窄、愚昧无知的人常有的恶念,因为除去自己的观念以外,他什么都无法理解,而同情、宽宥、理解则需要有他所不具备的人情练达作基础。在沙威心目中需不存在“宽容”二字,他只知一味盲目地恪守所谓的“职责”,法律在他的手中既使是被信手拿来读一读,《悲惨世界》也会因作者对正义的探求而打动人心,而有心的读者更会对小说繁复的内在结构赞叹不已,如同许许多多味。
变得面目全非。通过对沙威这个人物的刻画,作者揭示了美德的两面性。文学名著一样,小说《悲惨世界》值得被不同层次的各类读者反反复复地品
《悲惨世界》暗含的一个主题是通过善行使灵魂得到超度。书中有不少人物为不幸者施舍赈济。小说一开头,就以牧师的赈济教诲罪犯冉阿让学会仁慈确立了这一主题的重要地位,后来,冉阿让和珂赛特将同样的仁慈施予他人;而善良的马吕斯赈济了声名狼藉的德纳第一家。
《圣经》所倡导的其他美德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但没有哪种美德比爱在小说中表现得更为充分,雨果所指的爱不仅是浪漫蒂克的爱情,而且还有人类之爱,即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对于他的同类之爱,冉阿让心中的这种爱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正如小说中所描写,"主教使他的美德露出逐了地平线,而珂赛特则使他的美德喷薄而出。”作者在作品中闹明,没有爱,人们就无法生存;而没有爱而生存的人是精神扭曲的人,这种人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冉阿让只是在他从孤苦伶丁的小珂赛特身上寻找到自己的爱之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小珂赛特,并从她身上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以外的人生含义。由于小女孩对他的依赖和爱戴,冉阿让更深地体会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雨果对于如何运用洗练而有力的手法描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十分谙熟,他的诗歌、小说尽管有时不受批评家们的青睐,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人们总能为他博大的襟怀和炽热的情感所动容,以致在小说发表一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受到世界人民的深爱。雨果的一些诗歌、戏剧如今已被人们遗忘,人然而他的小说《悲惨世界》以及《巴黎圣母院》却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悲惨世界》的故事亘于拿破仑一世的衰亡,直至巴黎公社起义,整整二十余年时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要数作者描写细致入微,起伏跌宕的街垒战励
斗一场,作者巧妙地将马吕斯、沙威、爱泼妮娜等人编排在巴黎巷战的情节之中,使所有的人物受到这一历史大潮的荡涤。雨果总是能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场景之细节,从老太太在窗前挂上床垫以防流弹,到林荫大道上汹涌的人流。正是在这方面,雨果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匠心。同时他也没有放过每个人物挣扎的痛苦艰辛。作者在故事中将写人与状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书中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在混乱中的境遇使读者没齿难忘,小说最后几节毫不松懈,同样动人心魄地将故事引向其必然的结局。或许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和事的挖掘更有深度,狄更斯能更完全地把握生活之幽默;然而在表现人物内心痛苦与侧隐之心方面,以及在再现人们如何在当时历史的激流中搏击方面,雨果却完全可以与这两位大文豪媲美。
布鲁斯·D.里夫斯
(朱伟革 王新译 文溪 修华静校)